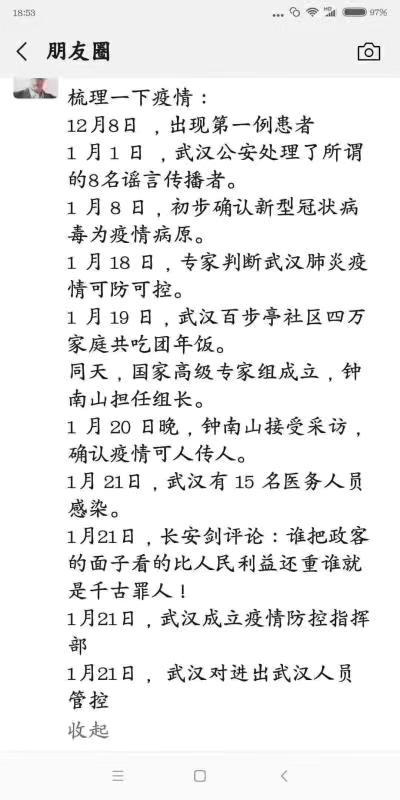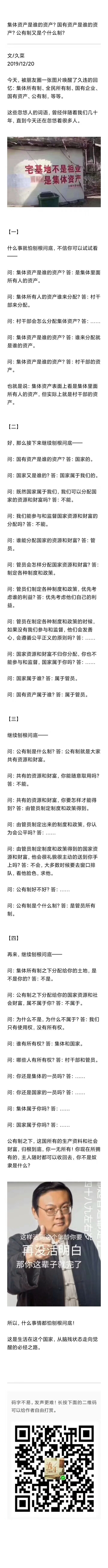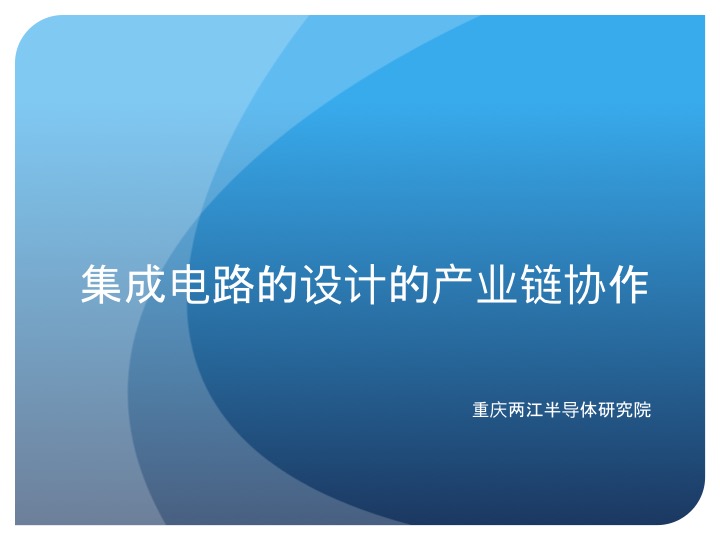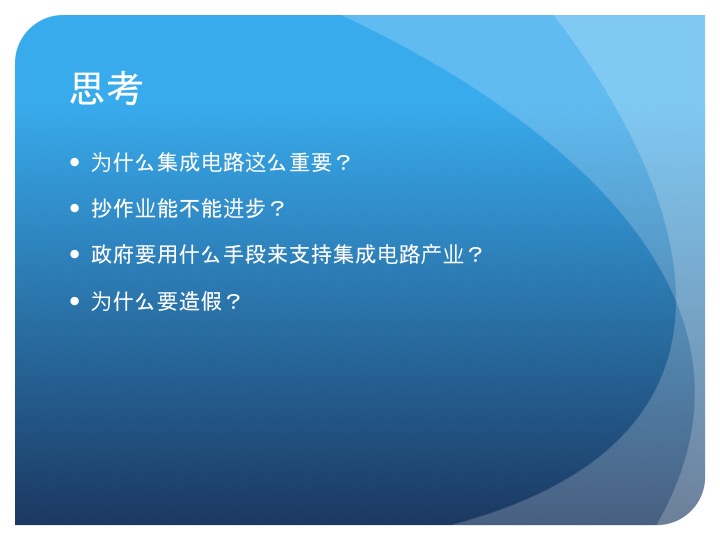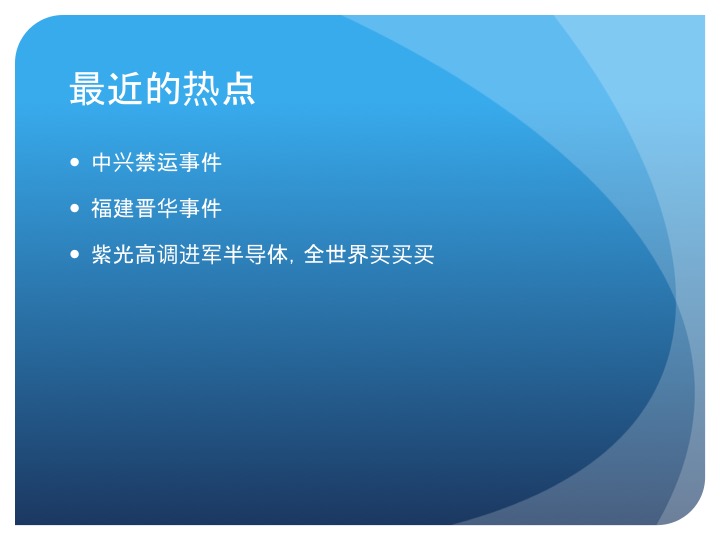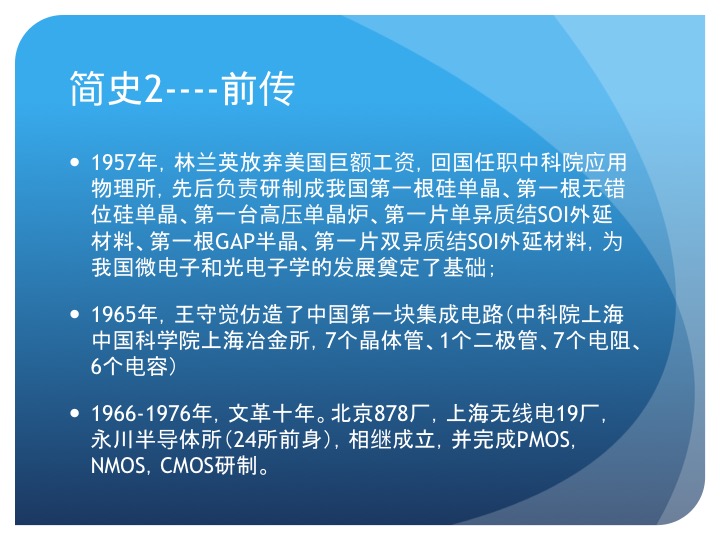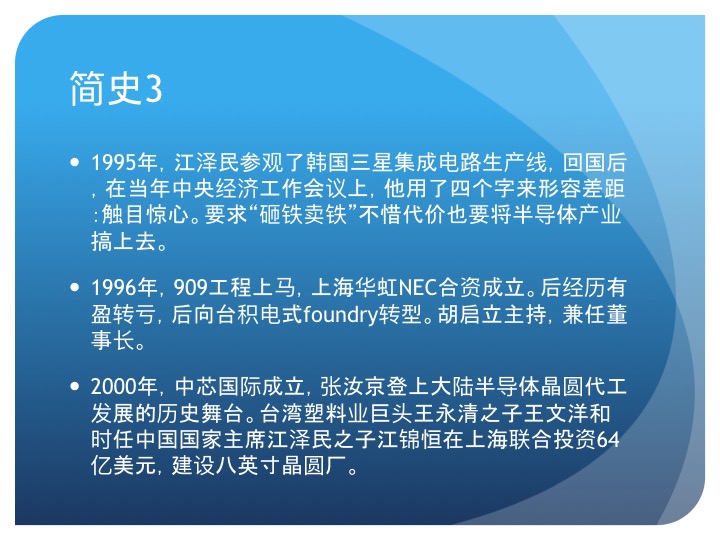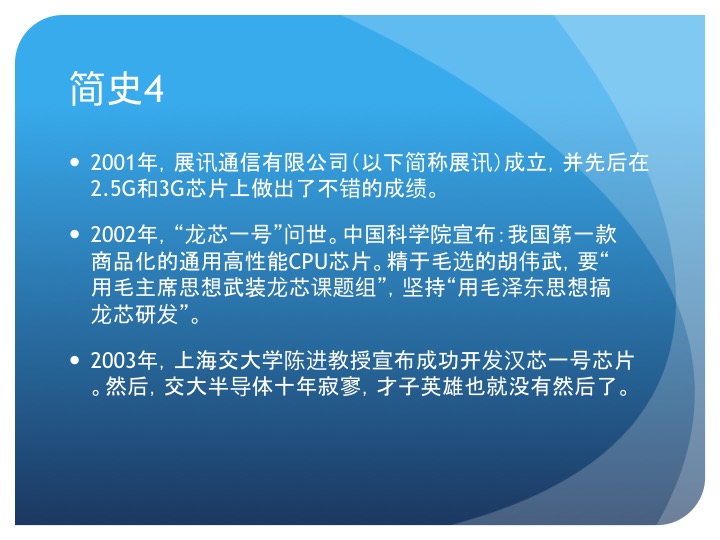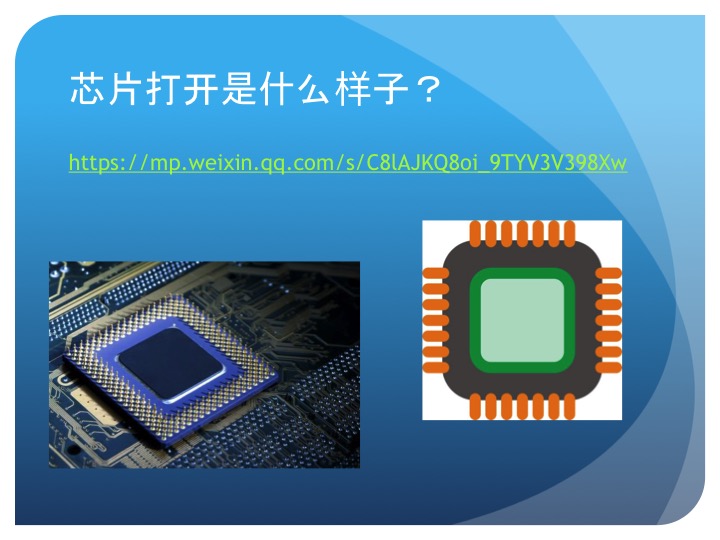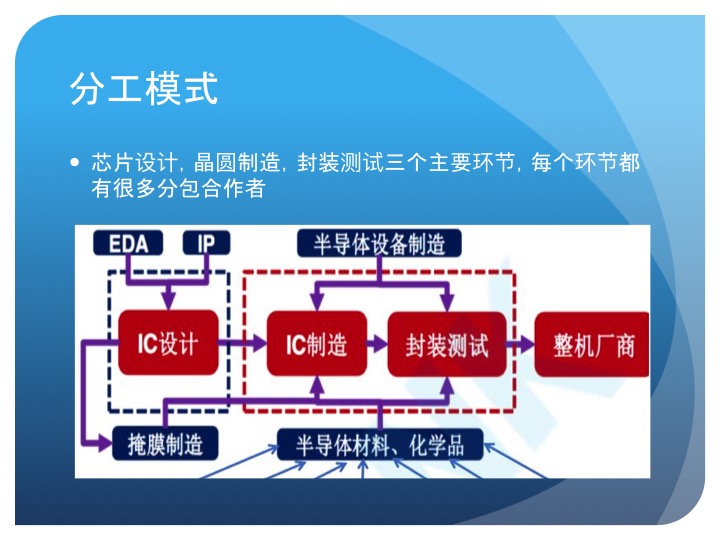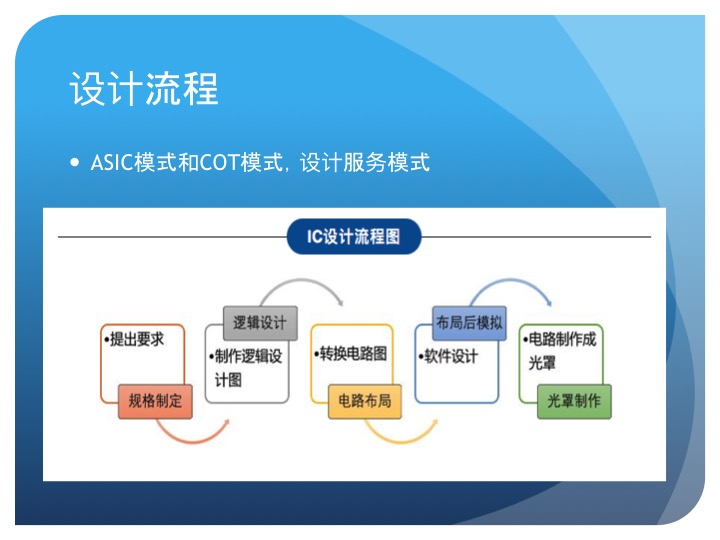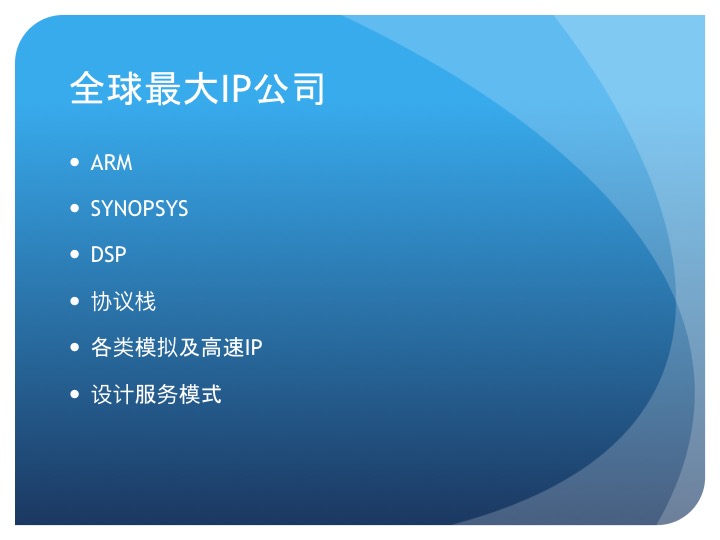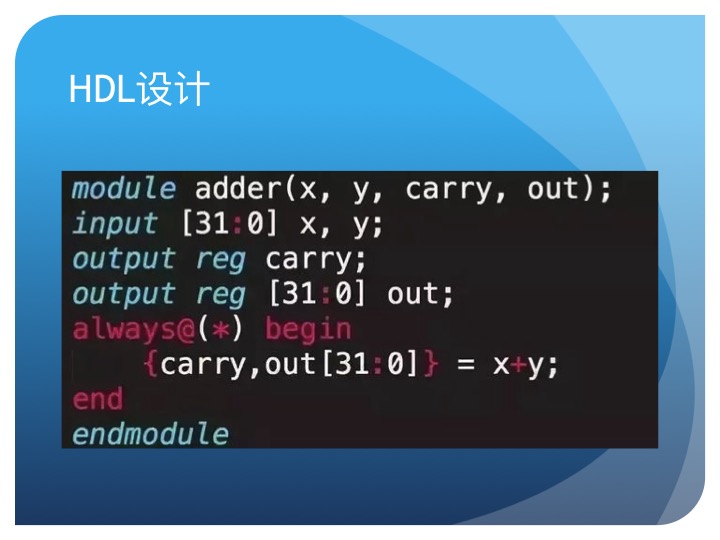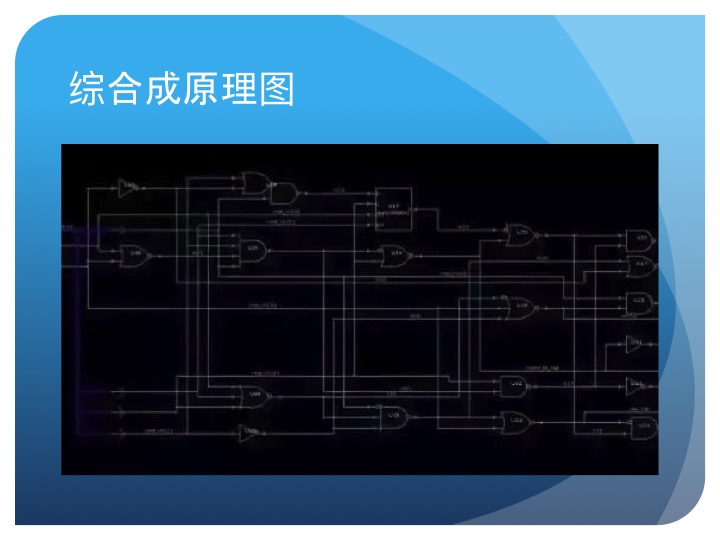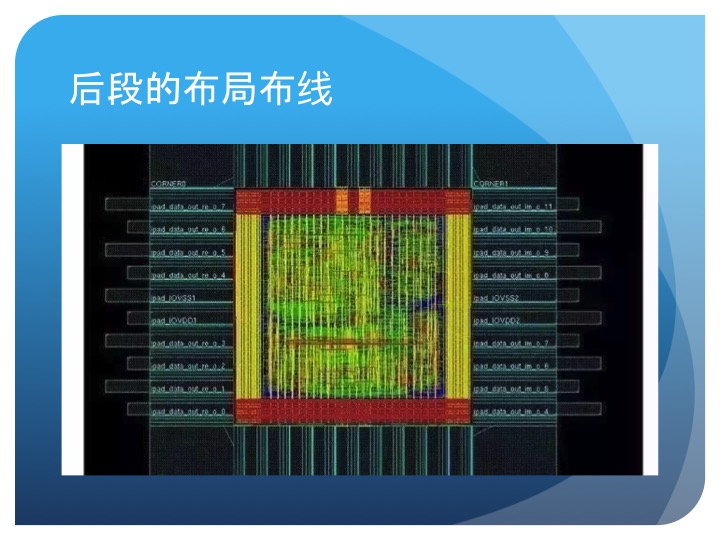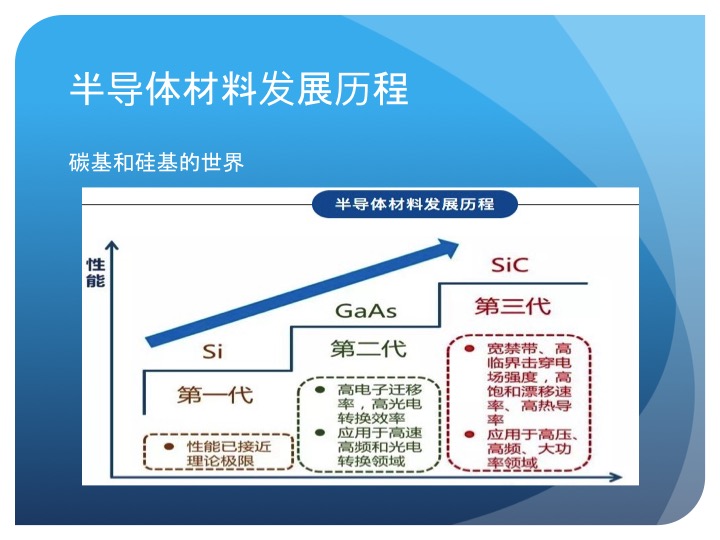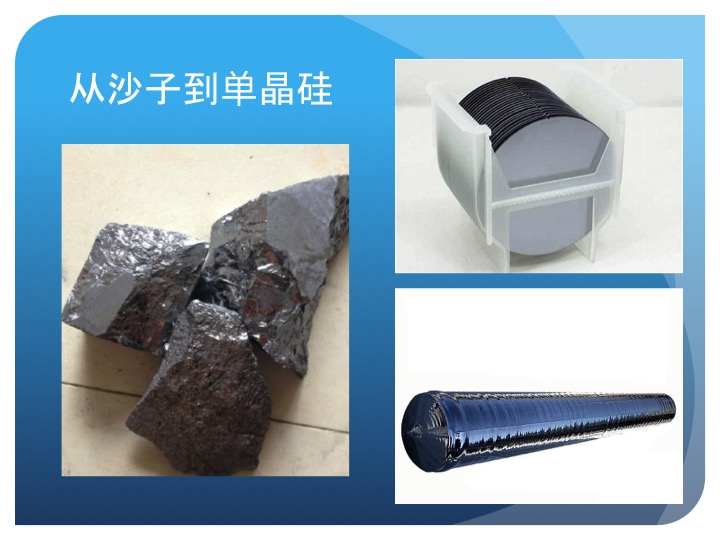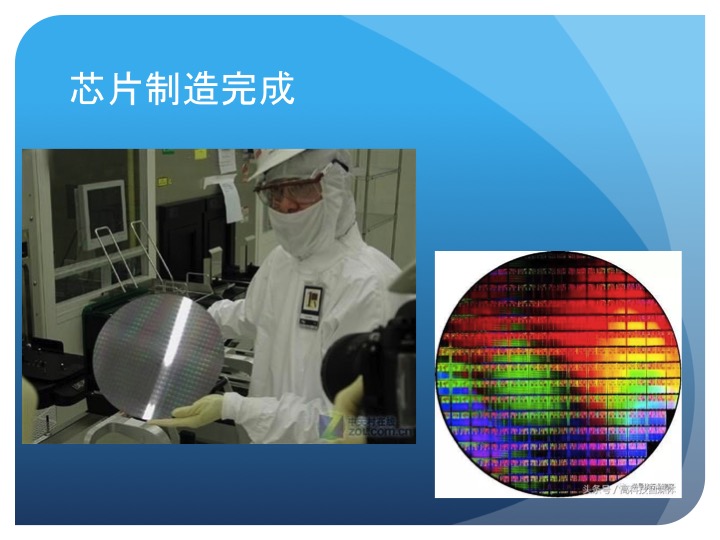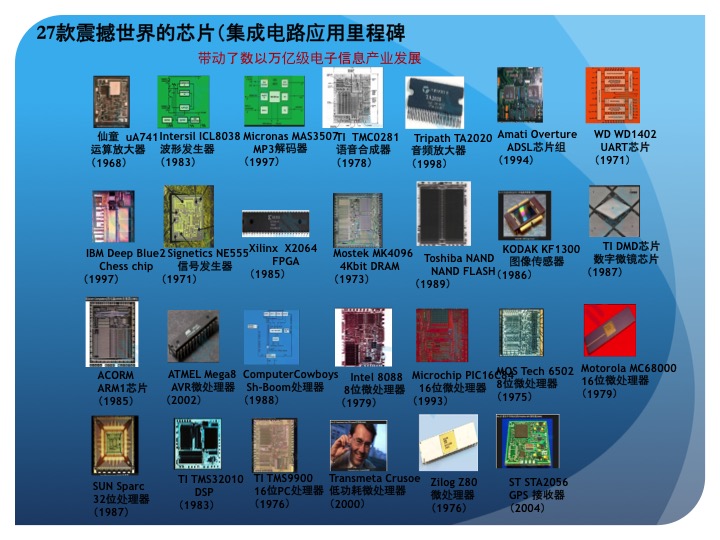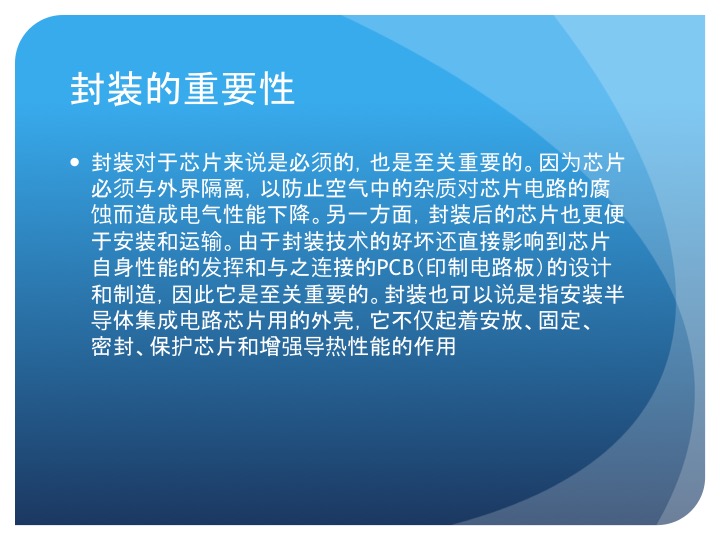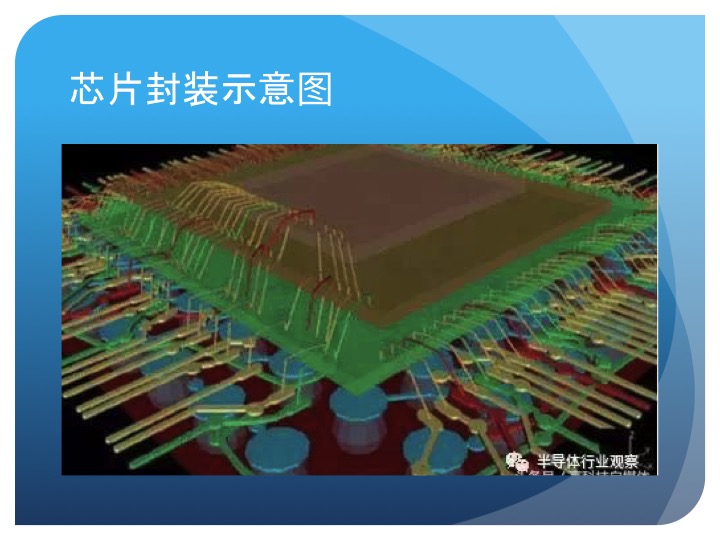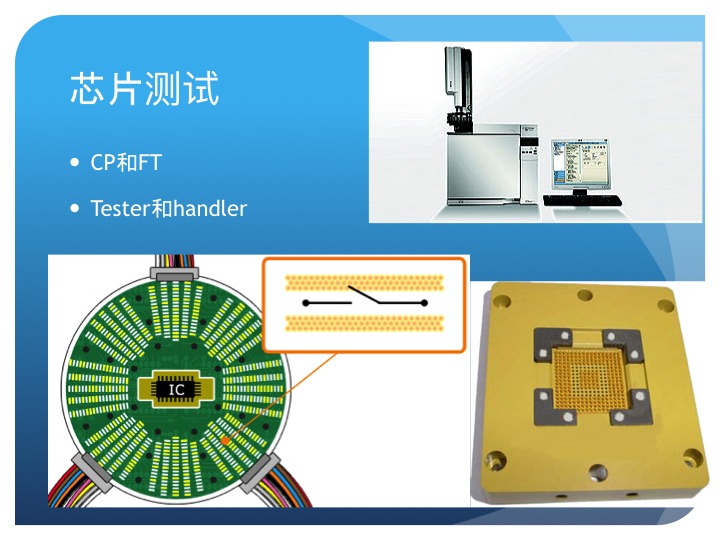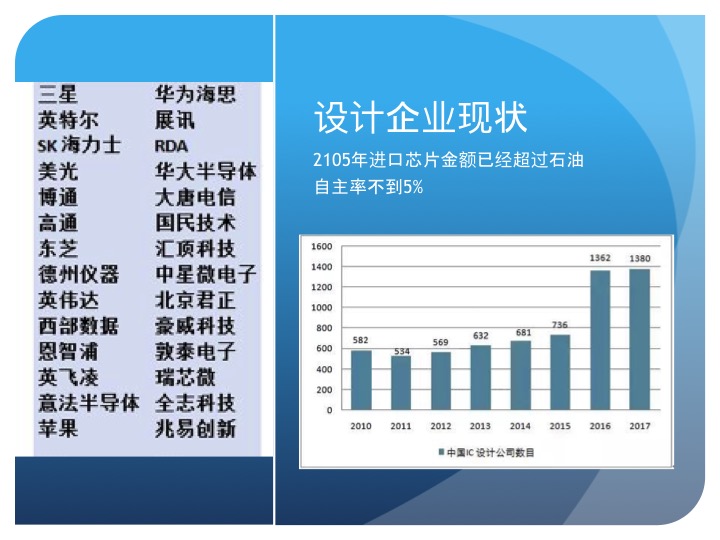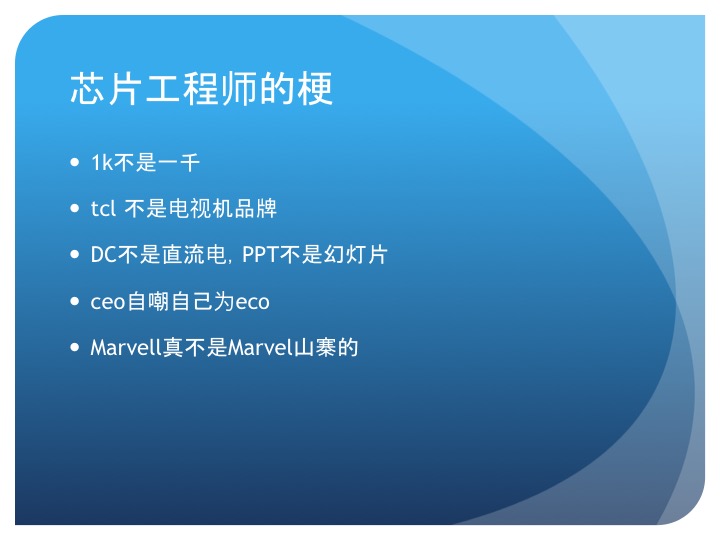开一门媒体素养/信息素养方面的课程,是我的心愿之一。这件事情已经有一些人在做了,而且有的人还做得非常酷,比如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门《Calling Bullshit In the Age of Big Data》——课名直译过来大概是“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分辨并驳斥狗屁”。
这门课由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开设,目前是一个学分,明年计划拓展到3-4个学分。授课老师是生物系的Carl Bergstrom和信息学院的Jevin West。
信息学院的老师讲这门课是很自然的,之所以还有一位生物系的老师参与,是因为这门课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关注的是科学中的狗屁,诸如用数据说谎、科学研究中的偏见和谬误等。
什么是“狗屁”
两位老师是这样定义“狗屁”的:
Bullshit involves language, statistical figures, data graphics, and other forms of presentation intended to persuade by impressing and overwhelming a reader or listener, with a blatant disregard for truth and logical coherence.
(狗屁指的是公然罔顾事实和逻辑的语言、统计数据、图表,以及其他呈现方式,它们的目的是让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并且让人难以抗拒。)
Calling bullshit is a speech act in which one publicly repudiates something objectionable. The scope of targets is broader than bullshit alone. You can call bullshit on bullshit, but you can also call bullshit on lies, treachery, trickery, or injustice.
(驳斥狗屁指的是公开批驳有问题的东西。驳斥的对象其实比狗屁更广,还可以包括谎言、背叛、诡计和不公。)
在大学课程的名字里面使用“狗屁”这种粗俗的语言,自然是颇为惊世骇俗的。在课程网站的问答部分,两位老师也作出了解释。他们说,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替代词,如果觉得“bullshit”这个词太粗俗的话,就用“bull”吧。不过他们也表示:
But let’s be honest: we like the fact that the term is profane. After all, profane language can have a certain rhetorical force. “I wish to express my reservations about your claim” doesn’t have the same impact as “I call bullshit!”
(实话说,我们看重的就是这个词的粗俗。毕竟,粗俗的语言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我希望对你的说法表达保留意见”远没有“你这就是放狗屁”有影响力。)
这门课的培养目标包括:
- 对你的信息食谱中出现的狗屁保持警惕;
- 无论何时何地遇到狗屁,能够识别出来;
- 能够准确说明为什么一则狗屁是狗屁;
- 能够在统计学或科学专业的人面前给出对狗屁的技术分析;
- 能够在迷信的阿姨和不自觉间表露出种族主义的叔叔面前分析狗屁,让他们能听懂,并且有说服力。
两位老师表示:这门课上学到的东西,肯定是你整个大学期间学到的最有用、应用范围最广的能力。
怎样教大家分辨和驳斥狗屁?
当然,在这个粗俗的课名之下,是非常严肃的课程设置。
两位老师在课程网站的教学大纲页面(http://callingbullshit.org/syllabus.html)公布了全部的课程内容和阅读材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阅读。以下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在引言部分,课程使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Harry Frankfurt的文章《On Bullshit》。其实他出版了一本书就叫《On Bullshit》。南方朔将其翻译成了中文,在台湾出版的时候用的书名是《放屁!名利雙收的捷徑》,在大陆出版的时候则用了非常保守的译名《论扯淡》。
第2周引入了一些常见的分辨狗屁的方法。第3周介绍的是孕育狗屁的生态系统,比如社交媒体如何促进了狗屁的传播,再比如TED演讲有时候兜售的是高端狗屁。
接下来的几周,课程从统计学和逻辑的角度切入,具体分析了一些狗屁的类型,包括混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中位数和平均数、“检察官谬误”等。课程还单独辟出一周介绍了数据可视化中常见的误导。
第7周的大数据部分,关注的是在大数据和算法的光鲜外表之下,“垃圾进、垃圾出”的现象,以及对机器学习的滥用、具备误导性的参数等。顺便说一句,这一周的扩展阅读材料正是会员通讯046介绍的《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其后几周深入科学研究领域,介绍了“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掠夺性发表(Predatory publishing)”等概念,以及学科之内、学科之间互相批评的伦理。
第11周是关于假新闻的。内容包括假新闻的经济驱动、回音室效应、如何进行事实核查等等,都是新闻实验室经常谈到的内容。如果这门课开设在新闻学院,那么这方面的内容足够扩展成整整一门课了。不过因为这门课的重点放在了科学上,所以新闻方面的内容被压缩到了一节课。
最后一周讲的是如何驳斥狗屁。针对不同的受众,需要用到不同的策略。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传播学中的说服效果研究,如果开设在传播学院同样可以拓展成整整一门课。
课程材料开放使用
这门课在2017年春季学期是第一次开设,它很快引起了网民及媒体的注意。很多人问:你们开这门课,是不是受到川普上台及“后真相时代”的刺激,想做点什么?
两位老师的回答是:并非如此。他们从2015年就开始准备这门课程了。“虽然这门课程今天看起来非常及时,但是我们不会评论当下的美国和世界政治。我们认为,如果人们可以识别出各个政治派别生产的狗屁,那么每个人都能过得更好。你可能不同意我们关于政府大小,以及美国干预国际事务的看法,没关系。我们只是希望,不管你的政治观点如何,你都可以抵制狗屁。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知道如何更好地判断信息,我们就可以作出更好的集体决策。”
在华盛顿大学,这门课极受欢迎。选课开始后,160个名额很快被抢光。两位老师收到了许多来信,以及出版社的出书邀请。
两位老师特别强调:欢迎其他学校的老师使用这些材料,开设课程。只有两个要求:一是注明出处,二是写信告诉他们自己是如何使用这些材料的。
所谓“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在英文世界里也有类似的说法——Brandolini定律:驳斥狗屁所需要的能量比创造狗屁需要的能量高了几个数量级。不过,两位老师认为:这一定律成立的前提,是人们不善于分辨狗屁。如果这门课可以使得更多人意识到身边大量存在着狗屁,并且学会分辨和驳斥狗屁,那么这条定律或许会发生改变:狗屁将变得越来越难以传播。
这当然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估计。也许过于乐观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去做,世界只会变得更糟糕。